生態思辨:身體與原民性之觀察與省思
教學工坊
2021-03-10
撰文/舞蹈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 朱靖文
「Critical Ecologies: Body and Indigeneity 生態思辨:身體與原民性」的課程,是TNUA台北國立藝術大學 X 蘇黎世藝術大學Shared Campus中的子項目,並獲得教育部北藝大深耕計畫以及USR(大學社會責任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計畫「Hi Five Plus從北投平埔族群到屏東原住民族的國際藝術對話」的補助支持。
從生命的動態找到生活的情態,我們思辨的生態可遠不只自然環境、人文社群,而是嘗試同理共感不同的生命故事和生活情境,在不斷流動的文化變遷中發現或說尋回情感的關係連結。我想這是在一片理性科學、資本市場大好的氛圍內,最難能可貴的事情。我們當然可以宣稱現代人所創造的社群同樣屬於一種「生態」,但關鍵正是多數時候我們並不以「生態」為之,所以是否屬於生態根本無所謂,反而是必須省問自己甚麼時候把生活週遭當作了生態。
親身體驗所謂原住民的部落是本堂課程內容的最終行程,在此之前,我們試著以身體工作、閱讀文本,包括何謂原民性(Indigeneity)、人類世(Anthropocene)、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南島民族的脈絡(History of Austronesian)、身體與公共空間的關係(Connection between body and public space),族繁不及備載,這些進入部落前閱讀的先輩知識著實不太容易理解,或者說它們不應該只是去理解,更多可能需要透過感官感受,一種身體層次的經驗,既使我們做的根本算不上是嚴謹研究中的田野工作,但是所謂學術研究者又能有多少機會,帶著自我的知識前去體驗截然不同的生活型態或樣貌呢?儘管我們再如何強調思辨,以文本討論生態,終究脫離不了,我們是如此地需要親身體驗。

(攝影:朱靖文)
為何是原住民的部落?我有一個官腔的回答,簡言之,是台灣的學術體系長期以來屬於外來知識體系的移植,清治、日治、國民政府都是,但說實在也無可厚非,最大的困境是由於學術體系似乎有意無意地與常民社會脫節(滿清與明漢、皇民與原漢、外省與本省),即便本土意識與在地鄉土文化的概念興起,學術體系的脫節現象也存在某種特定文化視角的距離感,同時更說明了研究者除必須拉近與常民的距離、甚至是邀請和鼓勵常民自己執行小研究,還必須不斷地回歸社會本身,無怪乎這堂課能夠進入補助企劃當中,畢竟想要瞭解生態,資料永遠不嫌多。
所以原住民的生命和部落的生活有甚麼特別嗎?不能是離島的小漁村嗎?不能是宮廟與江湖道士嗎?其實真沒有不行,台灣當代原住民的生活也沒辦法說多出彩,但他們正如你我一般,竭盡所能地在社會當中生存,有自己的社群活動與祭儀、有自己的社交行為與模式、有自己的社會價值與演變,當原住民試圖回歸部落型態時,我們透過參與及觀察或將文化轉譯成學術知識體系、或將精神轉化成生活信仰觀念,所以我們做的事也並不特別,只不過希冀以更遼闊和廣大的框架去看待島嶼上的人民、創造某種連結,因為我們確實不太一樣,而我們也確實都一樣地期盼島嶼的土地變得更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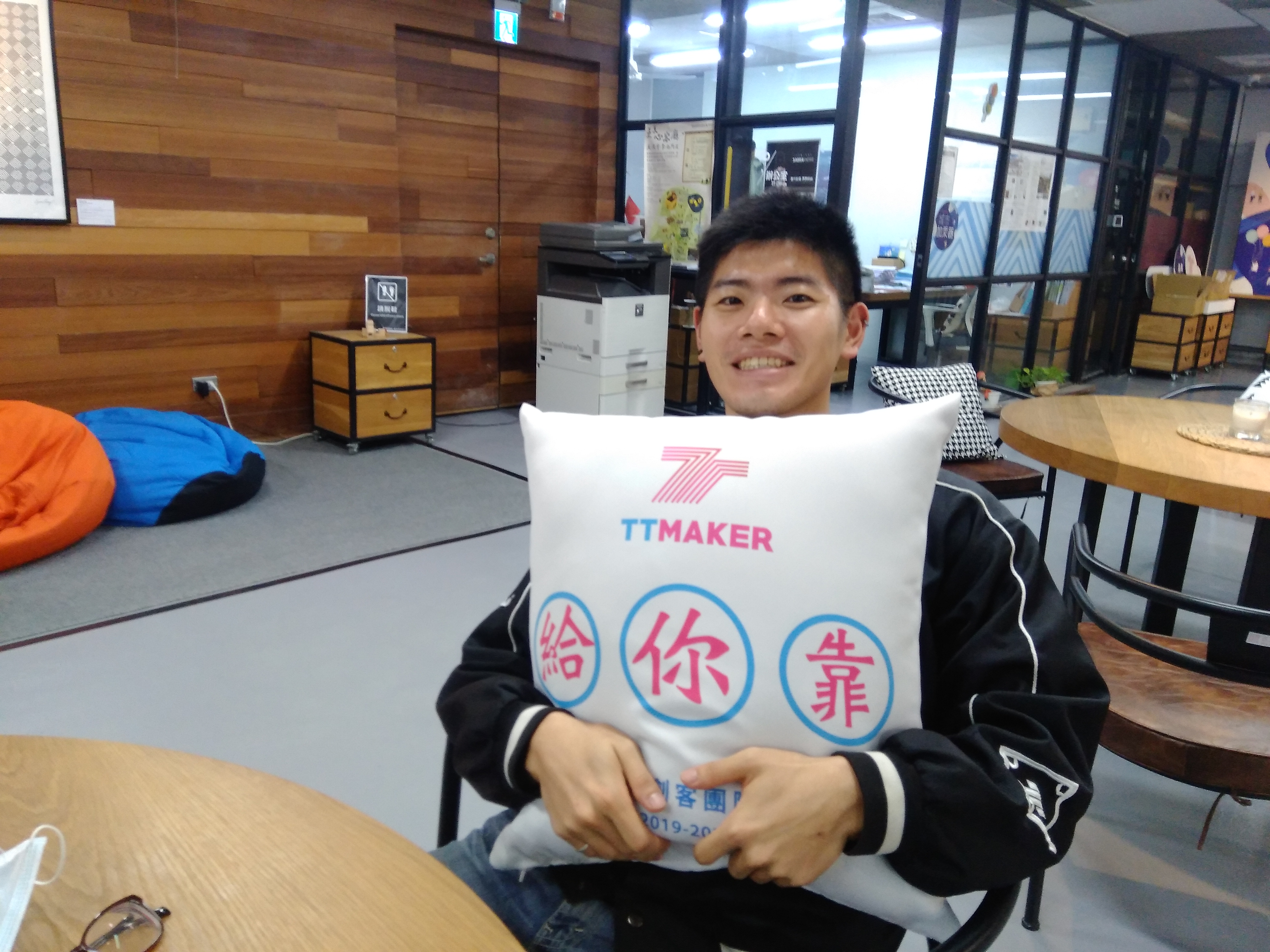
(攝影:林俊毅)
來台北念書生活將近八年,我很少會說台北是「家」,回宿舍、回租屋處的說法好像才符合心理狀態,大概都市化就是如此解離了一顆顆赤子之心吧?我這樣想。身為花蓮媽媽的客家孩子,每年農曆新年都會陪媽媽一同「回娘家」,那種奔波勞苦我在莊國鑫舞蹈團的身體上感受到了,所以我伴著它們歡騰歌舞,那些步伐和踢腿應該都是我近些日子最賣力卻也最不費力的身體活動,儘管膝蓋受傷前十字韌帶斷裂,在手牽著手的互相倚靠中、在齊聲歌唱的同頻呼吸中,每一下步伐和踢腿都是如此地沒有負擔,對我來說,群體性的舞蹈其實十分難得,多數時候我們必須面對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去尋找某種共同的路徑,然而這樣的機會更像是我們應該去接近那種共同,因為它早已存在於那裏,並非創造。
在冉而山劇場(Langasan Theatre)和 TAI 身體劇場的時候我其實很想回家,沒錯,花蓮是我第二個家,那種情感與土地的連結十分特別,就只不過是聽到團員除了對於部落有情感、也對於花蓮有情感,便已經勾起自己像條鮭魚優游的內心;在布拉瑞揚舞團(Bulareyaung Dance Company)的時候我想起五年前開始栽入接觸即興世界的場域,沒錯,就是在糖廠的那個空間,我開始奮力地跳舞,甚至最後影響了我唸研究所的選擇,就只不過是在一個熟悉的環境當中,那些關於初衷的記憶便捲土重來,彷彿正繼續呼喚我跳舞吧!沒甚麼好放棄的!隨後前往臺東縣原住民族文化創意產業聚落(TTICC,Taitung Indigenous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Park)時,我好像經歷了某種儀式,一種洗淨台北污身來到世外桃源的儀式,由於四年前落成後便成為古名伸舞蹈團接觸即興工作坊的據點,一年兩次,我每次都參與,今年也不意外,沒錯,我也在去年時感覺到台東成為我第三個家。

(攝影:朱靖文)
在高山舞集(在Puyuma普悠瑪部落中的Pinuyumayan卑南族花環部落學校)的日子,是熱烈歡迎、是熱切招待、是熱鬧暢談,我很難以一個形容詞去描寫這種情感連結,就姑且用「家」吧?因為這是一處回應土地的家、不需要血緣關係的家,曾幾何時,我們也依賴這種地緣關係建立彼此凝聚且共同相處的精神,在過去尚未都市化、交通革命的時代,來到現當代的日子,為甚麼有人會想提多元成家法案(2013)?其中的家屬制度更允許沒有血緣關係的兩人共組家庭,倘若因為相處而有需求能幫助彼此,走入體制內難道不好嗎?還是說我們僅能依靠精神性的情感去建立連結呢?
部落本身可以說是更大而包容的家庭,所以部落當然與漢族文化不同,而部落也與現今法理社會有差異,我們從部落的個體生命裡看見對家、土地、關係、精神文化的不同想像,我想這是生態思辨最有意義的部分。我們學習原民性,並且用身體去看見生活的情感與態度,以及生活的情態,生命不斷演替輪轉,流動是部落的生存法則,「生態」一詞尋求的並非自然抑或特別,而是唯有你看見不同,你才會回過頭看見自己周遭的生態,那個思辨的驅動力是彌足珍貴的。

(攝影:葉銘浩)

 電子報-藝游誌
電子報-藝游誌